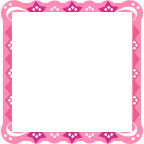“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 它既不寻求幸福, 也不逃避幸福, 它只是向前航行, 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 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
——莱蒙托夫《一只孤独的船》
- 相关阅读
“而野蜂终于飞过了大海。”
礼堂穹顶高高,水晶吊灯金黄的光碎满了地毯。人声往来、觥筹交错,香气四处漫淌,一场盛宴正当流动。恍惚间,女郎手里仿佛盛了一泓酒红色灯光,随着花枝乱颤的笑靥飞舞流转,映照成趣。
“小江现在出息啦!叔叔阿姨没有一起来吗?”酒宴入口处刚来了位新客人,一出手就送了巨额的礼金。新娘子迎上前灿烂笑着,大方道谢。
“真不好意思,他们以前的公司今天刚巧出了点事。”江隽带着歉意略一欠身,“这都清闲了几年了,碰巧就今天抽不出身。”
“没关系没关系,咱们这么熟的关系,不在乎这个。平时清闲就好啦,把以前少说的话都补回来吧……你现在当上部长了吧?我弟那家伙还只是底层打工仔呢。”新娘略含些自豪地打量他,亲近得像看自家人。
“而野蜂终于飞过了大海。”
“别这么说。”他无奈地笑起来,摆摆手道,“我那是小公司,没什么前途,不如程枳——说来他人呢?”
“嘁,他在里间躲着呢。这么大人了,还跟小孩儿似的怕应酬。关心他呀?也对,你们以前关系好。喏,从后园出去穿过小石子路就是了。你们叙叙旧吧,这边不要紧的。”
“谢谢程姐,新婚快乐。”江隽一弯眸,眼尾微微扬起,较常人浅些的瞳子里闪烁着令人愉悦的光彩,令简单的祝福也显得无比笃定。就像有些人天生擅长解数学题,社交上的才能也是他与生俱来的天分。
跟程家人想象的不同,他和程枳的关系并没有看起来那么无间,七年未谋面后,关心程枳就更谈不上了。很大程度上,虽然他不太愿意承认,今日抓住这个机会来访是有点好奇一篇小说的结局。
《孤船记》。他在心里将这三字默念了一遍,再次朝程枳的姐姐礼貌地欠身,推开了厅堂的小门。
“而野蜂终于飞过了大海。”
高中的文学社社团活动室仅有一扇灰蒙蒙的小窗,窗对面几步距离就是灰漆砖墙。窗下的圆桌就是程枳发现不久便沉迷得死心塌地的“圣地”。这里恰好处在走廊视野的死角,逃课坐在这写上一天小说也不会被路过的老师看见。
“最近在写什么?”
“《孤船记》。”程枳把半成品文稿缓缓推向他,“不过,怎么说呢,有点瓶颈。”
江隽没坐相地趴在圆桌上,用手指捻着纸张,心里感叹他写得真好,说出来的却是不知怎的成了:“这里有个错别字。”
“多谢提醒。”程枳提笔举到他面前画了个圈,又退回去。
“标题是取自莱蒙托夫那句话?但你着笔主要在主角和周围人的关系与情感交织上。”
“对。很矛盾,”程枳垂下眼睑,“所以我有点儿不知道该怎么写。”
“而野蜂终于飞过了大海。”
许澜光光最近的帖子,实际回复量基本都与数据不符(。)。
“我会从日光下的浪涛间飞越光阴,到时光尽头找到他。”
/南国势力爱情系/致郁系/哲理系专职文手。底线南国。
/最爱南国。接下来一起回家吧。
/常驻:家教圈,小说圈。
江隽嗅到了这句话里求助的意味,这在程枳身上并不多见。但——他又返回去读。必须承认的是文章完成度还很低,只几笔描绘了几个散乱的故事。
“你是想写他们原本是冤家,但在相处中逐渐互相理解,最后成了挚友?”
目前而言,写出来的部分确实只展示了这些。但程枳摇了摇头,缓慢地边想边说道:“或许……他们最终也不会成为挚友。甚至连互相理解也未必能做到。”
“所以是‘孤船’?”江隽一耸肩,“‘他即使与鸟儿一同长大,也学不会飞翔’……太消极了,虽然老古板评委的口味你肯定不在意,但和你化用的句子意境也不太搭吧。”
程枳叹了口气:“我还在改。”
那天这句话为他们的交谈画上了句号,而后来又发生了许多事。直到江隽看着白纸黑字被揉皱撕裂成纷纷白雪卷进天台风中,“全国一等奖”的字样在眼前一晃即走,吞没在五彩斑斓的世界里。他心里升腾起一种惨淡的快感,全然想象不到多年以后竟然会后悔一时冲动,没看到那篇文章最后的结局。
“而野蜂终于飞过了大海。”
程枳悬腕运笔,字如云雾,铺上纸面。思绪却腾云驾雾地向窗外飞,向着厅堂里微渺的宴会喧闹声去了。此刻他无比明晰地意识到:今日一逃可不仅逃了礼节性的送往迎来,还逃了与江隽的会面。
他和江隽当了三年同学六年校友,还相当巧合地搬家到了对门。关系谈不上好,高中毕业前更是闹得有点僵……但迄今已经七年未再相见,那些少年心性和脾气早已被时间的雨冲刷殆尽。他不大想在家人面前和江隽见面的原因和江隽本人倒没什么关系,只是条件反射般的阴影和无力。
“江隽这次又是班上第三,你能不能也沾沾跟人住对门的光?不要求你多拔尖,进个前十我和你爸也满足了呀。”
“诶,人家可努力呢,我书房窗户正好能看到,他书桌到晚上十一点爸妈都回来才熄灯呢,才初二就跟我这高二生同步,哪像程枳似的整天九点就开始在电脑上敲吧敲吧。”
“……”
“而野蜂终于飞过了大海。”
“……”
每逢饭桌批斗会时,程枳总是低头往嘴里塞饭,不反驳不争辩。和江隽不同,他不是那种很擅长撒娇讨巧或能言善辩的小孩,既无法哄顺父母姐姐的耳根,也无法把写作用堂皇的理由圆过去。至于江隽其实是拿着手机在书桌前打游戏这件事就更无法张口,想必只会收获更尖锐的“他打游戏怎么还学得比你好”。
不仅是学习,凡事一向如此。母亲和姐姐是彻头彻尾的“江隽派”,父亲极少对此发表意见,大约是觉得男孩子多打击打击也无妨。
那时江隽和他关系其实不差,对门又同班,一起上学放学吃晚饭,有时江隽会提议:“吃火锅吗?在对面,上公交307,两站就到。”
“回家路的反方向?”
“回去编个值日生的理由就好了。”江隽耸耸肩,“你去不去?”
“走。”
这些不得已而为之的同行与亲昵很多,日积月累着,虚情假意与真情实感也难免掺杂在一起。的确有那么些时候程枳脑中会迸发出“就这样下去也不错”的想法,萦绕着火锅酱料的香气。
“而野蜂终于飞过了大海。”
江隽心细,从不错过他的生日,而且总能不知从何处观察挑出他爱不释手的礼物。初三那年某日江隽突然在网上call他:“这个账号是你的吗?”
程枳看了眼截图:“是。你怎么找到的?”
“你发在空间那篇文章写得太好了,”江隽打字道,“我想上网搜搜是哪个作家来着,就搜到这个账号了。”
下个月的生日他便收到一本包装精美的书,硬质书封上作者处署的是他笔名。书页雪白,墨字漆黑,录进他账号里发布的所有作品,连随笔也编成合集组成一篇。他至今忘不了拆开礼物的惊喜欲狂,那大概真正是心脏因激动而战栗的感觉,一边忙着给江隽狂打下一连串谢谢,一边目光粘在书上下不来,枕着那本书睡了好一阵子。
“而野蜂终于飞过了大海。”
但到底是命运硬塞在一起的友情,偶尔的怦然欣喜总还是抵不过诸多性情不合导致的琐碎摩擦。今天刮一层皮,明天碰一鼻子灰,久而久之便千疮百孔。
初中时一次在食堂吃饭,正聊到兴奋处,江隽没过脑子地冒出一句:“像我这么两天打渔三天晒网地学习,真想不明白,后面的人得怎么学才能考得比我还差啊?”
程枳悬到嘴边的勺在原地一顿,漫不经心似的在空中晃了晃,才放进口中。
原本还要接着说什么的江隽猛地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讪讪缩回往前倾的上半身,垂头一副对碗里的米粒颇感兴趣的样子。
这些无意间刺人的话并不鲜见,但程枳从未反击过。他尚没能强大到不以为意,将这些云淡风轻地抛之脑后,只是他从来没有一副能与人唇枪舌战的好口才。每次他都试图宽慰自己江隽并非恶意,他想起某个夜晚。那天该是周五没错,因为只有周五江隽先走一步。程枳跟同学打球到暮色昏沉,而后一个人骑着单车回家顺便构思小说。谁曾想,骑着骑着就变成了构思小说顺便蹬两脚车,很不凑巧地蹬进了水沟的怀抱。
“而野蜂终于飞过了大海。”
在走廊里,他踌躇了几分钟,还是敲了江隽家的门。
江隽很快来开了门,浑身湿得一块一块的程枳虽然觉得很丢脸,但不得不交代前因后果:“骑自行车时走神,骑到水沟里去了。”
来路上他已经左右为难了半天,最后还是觉得,宁可被江隽嘲笑也好过被家里人唠叨好一周,并拎出江隽的谨慎专心作对比。
意外地,江隽没笑,也没问他为什么不回自己家,而是叹了口气:“有擦伤吗,要不要创可贴?进来洗个澡吧。”
程枳松了口气,发觉江隽虽然有时聊到兴头上会口无遮拦,但其实很善于捕捉和理解幽微的情绪。这个念头在他脑中一闪而过,随后他低头脱鞋进门。随江隽穿过明亮却空旷的客厅时,他难得想说句话缓和一下沉寂的空气:“你爸妈又不在家吗?”
“而野蜂终于飞过了大海。”
从小到大,他就没见过几次江隽的父母。明明住了十年对门,却在街上遇见也认不出。
“是啊。不过我外婆在呢,她睡得早。说话要小声一点哦。”
江隽走进卧室拿衣服和毛巾,留程枳在门外。卧室里没开灯,阴影锋利,切割大理石砖,他们被一分为二在光明与漆黑中。
“你希望他们回来吗?”
几秒后,黑暗中传来回应:“无所谓吧。反正从小就是这样,也习惯了。”
“父母工作太忙,平时只有个耳聋眼瞎的外婆在家里,哪有人教过他人情世故呢?”他还记得曾经无意间听到的父母的谈话。他们寓于话语间的怜悯莫名刺痛了他,那里面含着一种没来由的居高临下。电光石火间,他突然想到,江隽一定是不愿被怜悯的。所以他争强好胜,要站到高处,以俯瞰的姿态使那些怜悯烟消云散。
程枳微微垂下眼睑。他看到身后吊灯光明炽热,将他的影子不断推向前,融进卧室地板的黑影里浑然难分。
“而野蜂终于飞过了大海。”
出口处柜台上摆了满满一篓子柠檬糖。这是程枳喜欢的口味。江隽脚步一顿,随手捞了一把,才走进后园里。
大约很久无人走这条路了。不久前下过雨,道旁未修剪的观赏木已经挤兑起行人的空间,江隽稍不留神就蹭落一汪水露。小路上坑坑洼洼,夜里虽一片漆黑,但大抵能猜出是腐叶枝杆一类,又泞又滑,土腥气熏人。这倒并不令他反恶,这条路和高中里那条很像,勾他错觉又回到了他所思念的岁月里。
江隽拨开头顶的蛛网,总算站在了园房门前。无端地,他有点微妙的踌躇,就好像……近乡情怯。
中考时他年少倨傲,放弃了市里最好的高中,高分数线十几分去了离家近的二中实验班,与堪堪压线的程枳又做了校友。他像一棵树吸饱了雨水,不但个子开始飞快拔高,性格也一日千里地变化着。最显著的就是他嘴角总是噙一抹笑意,越来越少像初中那样无意中透漏出令人不悦的真实想法。
“而野蜂终于飞过了大海。”
他的人缘爆发式地攀升,无论去哪总有几个人愿意同往,和程枳的交往自然占的时间愈发少。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维持了不远不近的平衡关系,像蛛丝联结的两端,因微细若无而幸免于风浪。
直到高二末以前,他俩间最值得一提的联系大概只有江隽外婆的去世。
那是个冬天,程枳记得很清楚。老人总是难熬过冬天。他们的城市正坐落在不尴不尬不南不北的纬度,冬天下雪与否的概率各占百分五十,全看天公心情。那年格外冷,下了场被媒体誉为十年一遇的暴风雪。那天程枳上完补习班放学,死命攥着飘摇挣扎的雨伞,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从积满雪的路上挪回家。两家大门都敞开着,程枳看到许多不认识的大人堵在江隽家的客厅里。
“而野蜂终于飞过了大海。”
他发现自己的答案是无所谓。人们为亲人的死亡悲痛欲绝,往往不是因为死亡本身,而是无法接受离别、永诀。但对他而言,并没有什么离别不能被接受,他唯独离不开的只有他自己而已。
“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随时说。”最后他干巴巴地说。江隽微微一点头,什么也没说。
回到家里母亲正煮饭。他向自己的卧室走去,经过厨房时母亲问:“不多跟江隽聊聊天?”
“我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而且如果是我的话,现在大概更想自己一个人待着吧。”程枳心不在焉地说了真心话,推开门拿下书包,弯腰将包放到地上。
“你这孩子太冷漠了。”母亲在他背后说,“如果是我或者你爹死了你估计都不会像江隽一样难过吧。”
程枳松开书包袋子,慢慢直起身。他突然觉得胸腔里有个漏斗,砂砾慢慢地倾泻,堆在心脏上形成一个小小的山包,叫人窒息。桌面上水笔凌乱地丢在本册间,荧光笔的笔盖也没关上,早上翻开记灵感的小本子忘记塞到书堆最下方了。
怎么乱七八糟的,全都放不对地方呢?他想,得好好整理一下了。就现在。
“而野蜂终于飞过了大海。”
天啊天啊回来考古居然看见熟人啦 还记得你以前是我们工作室的 我以前的号都找不到啦
今日头条
- . 【調皮】画图、游戏、纪录
- . 【带vlog】小孙の奥奇之旅
- . 搭配帖aaa
- . 【真渊】行者无疆
- . 【记录】再逢烟火时
- . 【与你揽月】2024
- . 【阿夏勒】一些搭配,都是很华丽的一些搭配
- . 【开荒选谁好】
热门专题
+-

- . 积分商城上新啦!
- . 非遗联动版本《粤韵芳华》
- . 粤韵探寻H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