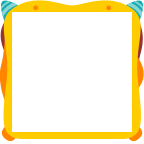Merry bad ending
安涉斯/伊莱。
水珠从她的发丝里滴落。
安涉斯垂下头,盯着它们在自己的大腿上微微映出傍晚深蓝色的光,然后在自己的刻意颤动下滑落,留下不太明晰的水痕。她伸手攥住颊侧的一缕头发,企图紧攫它们来排干藏匿在小小间隙里面的液滴。掌纹之间凝聚的积水像是那片荒远的、丛生着断裂的躯干和风干的眼珠的土地之间积存着血液的小水洼。
淡红色,她想。无边无际的淡红色,如同滔天巨浪般地向她倾泻下来。海浪没顶,她的肌肤在海水里感受到一点麻木的温存。金属与水压拉拽推搡着她向下坠落。无论看得到、看不到,她快要眦裂的眼睛传递给神经的是一片红色。浅淡的红色,几乎要隐没在落日烧红的烙铁一样的街道里。
伊莱捧起她的头发,吹风机在她耳后嗡嗡作响,而暖风从她的脖颈向两侧逸散。现在她的后颈从海床上拔起,成为一湾浅白色的临海沙滩。伊莱的手指在安涉斯的发丝间穿梭,她能听到指尖与头皮和发丝摩擦的沙沙声。水分从发尖开始枯涸。安涉斯轻轻梳着发梢,看着它们被手指带起些许皱纹增加的圆形。湿润的面部还没有因为水分的蒸发而失去稍暖的温度,惬意的灼热在鼻子深处悄悄蕴藏着。
“伊莱,你看?”她说。在稍微破损的毛边的记忆里伊莱好像并没有从她的身侧弯下腰来,用温和的眼睛注视着她。本应是那样的,目光轻柔得像是浅海里随波逐流的水草,又平稳地像是星宿,闭上双眼时旋转的无尽的蓝紫色的星云。
安涉斯从坑坑洼洼的柏油路面上坐直身体,温暖的晚风从她身后略过,她偏头看见自己头发微微向前飘起。那时太阳将要落下,红色的章鱼卷曲腕足,攫取灰尘污迹与波动的空气,坠亡地平线。一切都是红色的。她浅粉色的头发被义无反顾般的溅射出的红色染料洇红,在最后的末端留下一小截金色。夕阳的色彩与光亮不太刺眼,她抬起头向上看,空荡荡的天空,甜橙色,干净通透,流淌着落日在今天的末尾还带着余温的血液。
“很温暖。”她听到伊莱这么说。
安涉斯闭了闭眼睛,头发干的差不多了,她想,吹风机比这样麻烦多啦。大腿上还有着不太明晰的水痕,微微反射出一点金属般的光泽。金属膝盖的表面已经被磨得有点粗糙,上面有被各种东西留下的细小的划痕,不过这并不妨碍她低下头从那一小块地方看着弯曲的窗户和深蓝色的夜空。安涉斯变形的脸也和窗户嵌在一起,但在黑暗中看不大清楚,只有从窗户射进来的街灯的光穿过最外围的发丝,她的轮廓淡淡地亮着。
然后她很慢、很慢地垂下头。伊莱微微闭着眼睛,仍旧没有用那双温和的眼睛注视她。淡红色枯萎凋零,隐没在黑夜最深的背景。
安涉斯看着他的头颅,完完整整的,虽然被涂抹上了灰尘的污迹和淡红色伤痕。“伊莱,”她说,最终失去下文。
直到雪白的泡沫湮没海岸线。
春
-
凌晨四点,时钟在镜子里面微微泛光。长谷川坐在我的床边,眼睛里面缀着不曾熄灭的破旧霓虹看板的浅红碎钻,脸颊上铺展着街灯的橘黄色柔光。厚重的深蓝色阴影埋入她的颈窝。
“没事的,”她吻我的额头,“我在这里,你会战胜黑狗的。”于是我的前额上伸展出一枝樱花,倒立在她的视网膜里盛开。浅粉色的重瓣,飘摇、颠颤、零落。她樱花色的上唇。此刻我的脑海里只剩樱花。她沉默而柔和,与我周边的一切融为一体。去年春天她不在这里时的樱花,今春宿醉后快要呕吐前看到的樱花,破碎晕染的粉色,和她。
“春树,你是樱花,是姐姐。”我说。房间里晦暗的光像是我四周渊默的峡湾,只有她的轮廓细密地缝上浓厚的橙色,如同初升的太阳,又露出新生的皮肤那样不堪狎昵的色彩。
“是真的吗?”她说,唇角溢出麦芽糖般光亮的笑。
“是真的。”我肯定地回答。
“那我可真高兴啊。”她又忽然意识到了什么,俯下上身,缓缓凑近我的脸庞。我能听到她的呼吸,昨冬的海潮在她的唇齿间还未退去,由于短短的上唇与下唇紧紧抿着,只好从鼻腔中呼出渐暖的海风。“好些了吗?现在......不,是刚才,心情平静着吗?”
我在深蓝色中匿笑,“在我刚刚醒来,长谷川亲吻我的额头的时候,大概退潮了几秒钟。所以我想起了樱花。”
她抬手将碎发别在耳后,直起身子再次被涂抹上橙黄色的光。浅栗色的头发将要熔化在里面,流淌成光的河流。她捏住我的鼻翼,句子里稍带着一点不怀好意和略微轻松的上扬的尾音:“真狡猾呀,理象。不过要我说,这是一个好兆头,对吧?几秒钟会变成几分钟、几小时、几天,甚至永远,你会好的。但又说回来,别再把我当做你的联想结合体啦。”
鼻头的压痛喊着抗议,从鼻孔的狭缝里勉强挤出“嘶嘶”的空气。“快放手,樱花姐姐。我累了。不过今天早上吃什么?”
长谷川从善如流地松开手指,但温热的指腹轻轻抵住我的鼻尖。“现在是凌晨四点钟,你就开始想念早餐了吗?快闭上眼睛。”
“我睡不着。但是我感觉好些了。“我伸出手抓住她的食指,拇指触到她指尖的薄茧。“你昨晚......晚上睡了吗?现在是凌晨四点。”我重复她的话。
她的手指屈了屈,圆润的指甲陷在了虎口里面。“我睡过了。”她说,春潮带来的风从我颊边拂过远去。
黑暗中有什么东西向我扑过来。我闻得到纤维与植物根茎的腐烂味道,深埋地下六英尺的土腥气。我阖了阖眼睛,墙上的海报正在扩军,眼前胶片上的颗粒就快要聚集成星云了,我想。
“晚安。”我说,为了逃避避无可避的恐怖幻想。然后终于听到她坐上床边时布料摩擦的窸窸窣窣的声音。
“晚安。再安静地躺一会儿吧,现在是凌晨四点钟。”
她又轻声补充:“我在这里。”
*含有不准确的抑郁症症状描写。绝大部分对其的描述都借鉴或化用于英国作家马特·海格的《活下去的理由》。
*时间线在上一篇之前。
冬。
-
痛苦消失了吗。
我仰起头,感受到发丝掠过脸颊浮动,如同哑声呼救的疲软的神经末梢,海月水母般在海水中随波逐流。呼出的水泡向上升、向上升,破碎在视野上方的深蓝色里。我想起影子,炽烈的阳光下的深蓝色的影子。沙滩反射着阳光,明亮成纸白色的、一望无际的海滩袒露出平整的胸腹。赤裸的双脚埋入圆润细锐的沙砾。泛红的脚趾和它们熔化在一起。
进行外科手术的幻觉,破颅而入、剖腹剜心的手术刀划开我光赤在外的皮肤。无影灯又变成太阳,我的影子是乌鸫,在脚边无声逡巡。
惊恐溶解在海水里。苦水灌入我的耳道和气管,左耳廓的细语液化成酸,腐蚀昏死的鼓膜。心脏失常地跳动,想要破胸而出,但海水深压我的前胸,鼓点持续慌乱。而过去我所欢忭的:她短而柔软的樱花色上唇、微雨和夕阳,短暂地浮现,塑化成颗粒,随着波浪涌离。
海水漫入口腔与鼻腔,气泡消弭之后自然地呼吸如同与水合流。我缓慢地下沉、下沉。深蓝色里我即将面临休克吗?大脑也许可以停止转动了。
“醒来,理象。醒来。”我听到长谷川的的嗓音,模糊而遥远的、悲戚而不确定的,她的嗓音。
海潮卷起我的灵魂同着碎浪送回。我没有溺水,没有下沉,没有在成为几天后肿胀的浮尸,大脑也从未停止运转。
她的胳膊环着我的肩膀,炽热的体温仍旧失真。我们失去了支撑和呼吸,瘫坐在海滩上。四周的深渊破碎,我在迷蒙中感受到细雨下落,溶解着皮肤与肌肉的纤维。
我别过头,呕吐了一地。不是海水。啊,不是海水。
呕吐物冲出我的胃。从食道延伸出的酸冽和干辣。
“我在这里……我在这儿。别怕,会好的,会好的。”她仍然在重复无望而悲伤的絮语,脊背的刺痛感再次传递到每一处神经的末梢。我紧攫她的手臂,痛感却凝固在指尖,终于在她的体温中汽化。沙滩上的氧气太过稀薄,似乎比拟它们在珠峰八千米以上游弋的同类。“我会成为路标吗?”我问她。
“你不会,你是理象,还在这里的理象……下雨了,对吧?下雨了,我们回家吧?”
我想要回答她。但舌头又在忽然之间停止了运作。我漂浮在外凝视我的身躯,我被隔离着。于是我看到理象失语的模样。她茫然无措地望着微雨时灰色的天际线。风从远海吹来,带着一股苦味。我存在的证据,她要求的证明,冲刷殆尽,雪白的骸骨,魔鬼,巨大的黑狗,气塞,苦味开始变得酸馊,后颈的疼痛和颤动。我在坠落,向着地心。
我哭了。
不仅仅是因为刺痛,还有别的东西。但是从眼泪里蒸发出来的、回不去的咸涩的晶体,留在手掌心里,硫酸般没入腐蚀肌肤腠理,顺着血管流回心脏,刺痛心房。碳化的手掌焦灼着尖叫:
痛、痛、痛。
于是泪水又滴入掌心,汽化出白色的烟缕,刺激黏膜上的纤毛。我在睡着之前想,那是烧融的塑料吗?
她背对着窗户。燃烧殆尽的余晖俯冲到她身上,于是她的轮廓短暂地泛起灰红色的光,余下被黄昏吞没的深黑色阴影。
盛夏的八点钟,向阳阖了阖眼。黯淡的光线仍旧不能涂绘她的容色。楼下街道的蝉鸣躁动着融化,“噗”地冒出气泡。耳道里塞满鼓鼓囊囊的背景音,他低低哼了一声,嗓音在牛皮鼓面下跳转回荡,敲击成闷响。
“妈妈,”他说,“他今晚会回来的。”
然后他缓慢地微笑起来。被右手松松垮垮握住的书包在地板上拖曳着,蹭过泥迹已干的鞋印与蜿蜒的水痕。房间里潮湿的地方有浅淡的消毒水的味道,同热气混合着被吸入鼻腔。大脑在浑浊的气味里晕头转向。
今日头条
- . 【調皮】画图、游戏、纪录
- . 【带vlog】小孙の奥奇之旅
- . 搭配帖aaa
- . 【真渊】行者无疆
- . 【记录】再逢烟火时
- . 【与你揽月】2024
- . 【阿夏勒】一些搭配,都是很华丽的一些搭配
- . 【开荒选谁好】
热门专题
+-

- . 积分商城上新啦!
- . 非遗联动版本《粤韵芳华》
- . 粤韵探寻H5